婴儿落地的第一声啼哭,像是命运的某种暗示。
那皱巴巴的小脸涨得通红,挥舞着拳头仿佛在抗议什么——后来我们才明白,这声啼哭预告了整个人生:功课重压下的少年会在深夜里偷哭,中年人在酒局散场后蹲在路边干呕,老人握着诊断书的手止不住发抖。
我们似乎永远在和某种看不见的东西较劲,这让人忍不住想问:既然活着这么苦,为什么我们还要来这世上走一遭?
人一生的目的和意义究竟何在?
前年探望临终的堂哥时,他突然紧紧攥住我的手。
癌细胞啃食的躯体轻得像片枯叶,眼睛却亮得吓人:"我这辈子啊,就像在雾里走山路,摔了无数跟头。
现在雾要散了,倒看清那些绊脚石都是路标..."他的话让我想起老家后山的木麻黄,越是寒冬腊月,越是长得茂盛。
看看我们周围的世界吧。
东京湾的渔民望着检测仪上的辐射首发愁,华尔街的实习生躲在卫生间吞抗焦虑药,亚马逊雨林里,土著女孩抱着焦黑的树桩掉眼泪。
这些相隔万里的苦难,像被无形的线串成了念珠。
有人觉得这是老天爷在惩罚人类,我倒觉得更像是母亲在给迷路的孩子留记号——金融风暴卷走的不只是钞票,还刮掉了我们脸上的面具;地震摇塌的不光是房子,更晃醒了麻木的心。
我经常听叔叔们给我讲,说早年间村里闹饥荒,饿得啃树皮的人反而更舍得把最后半碗粥分给邻家孕妇。
现在日子好了,住对门五年的邻居见面只会刷指纹锁。
地铁里人人都捧着发光的屏幕,却对身边哭闹的孩子视而不见。
我们发明了能跨洋视频的手机,却治不好心里那个漏风的窟窿。
这让我想起爷爷常说的一句话:"蜂群要是忘了为什么采蜜,再多蜂巢也会垮。
"老人们常说"天无绝人之路",可看看新闻:冰川在流泪,战火在蔓延,病毒换了新花样,年轻人的眼睛越来越空。
有人躲进虚拟世界当英雄,有人在首播间拼命卖笑,更多人在凌晨三点刷着短视频失眠。
我们像被困在玻璃罩里的飞蛾,明明西处碰壁,还要假装在跳舞。
但您注意过雨后工地上的野花吗?
混凝土裂缝里钻出的蒲公英,硬是在钢筋水泥里开出一朵太阳。
我家楼下修车的老张,独子车祸走了之后,把破车库改成了流浪猫收容所。
他说:"以前总嫌儿子玩物丧志,现在听着猫叫,倒像他又在屋里打游戏。
"苦难这东西,像把双刃剑,有人被它劈碎了脊梁,有人却用它雕出了光。
记得《死海古卷》里约伯的故事吗?
那个失去一切的义人,最后在粪堆里与造物主对话。
不是说非要吃尽苦头才能开悟,而是当生活撕掉所有伪装,我们反而能触摸到最本质的东西。
就像被退稿十二次的J.K.罗琳在咖啡馆写《哈利波特》,梵高在精神病院画《星月夜》,司马迁受宫刑后著《史记》。
这些故事不是在歌颂苦难,而是提醒我们:最深的光,往往诞生在最黑的夜。
有个现象挺有意思:汶川地震后,成都人开始流行在阳台种花;疫情隔离期间,对面楼的钢琴声突然多了起来。
苦难像块试金石,逼着我们在废墟里找生机。
这让我想起老家烧陶的土窑,胚子要经过烈火烧、冷水激,才能从一滩烂泥变成能装月光的青瓷。
科学家说量子纠缠证明万物相连,佛家讲"一即一切",其实都在说同一个理儿。
华尔街的股灾会让云南茶农皱眉,澳洲山火的烟尘能飘到南极企鹅的羽毛上。
我们习惯把苦难分装在不同的盒子里:这是天灾,那是人祸;这是私事,那是公案。
可就像打碎的镜子,每一片残渣都映着完整的天空。
这本书不想教你怎么逃避苦难——毕竟该淋的雨总会湿透衣衫。
我们想说的是,当大雨倾盆时,除了抱头鼠窜,还可以仰起脸尝尝雨水的滋味。
那些在ICU外守夜的人,在扶贫路上摔跤的干部,在流水线上偷背单词的打工妹...他们身上有种共同的东西,像暗夜里的萤火虫,越是黑暗,越是明亮。
当您看完本书的内容,您可能会发现:医院长廊里的消毒水味和寺院香火的气息,本质上都是生命的味道;农民工结满老茧的手和钢琴家修长的手指,弹奏的是同一种生存的乐章。
金融海啸不是数字游戏,是千万个家庭在风暴中抓紧彼此的手;地震不单是板块移动,是让我们重新思考该把什么砌进生活的基石。
说到底,苦难像把钥匙,不是用来打开某扇具体的门,而是帮我们看清——原来自己本就站在光明里。
新生儿的第一声哭喊,或许不是恐惧的哀鸣,而是灵魂在说:"我准备好了。
"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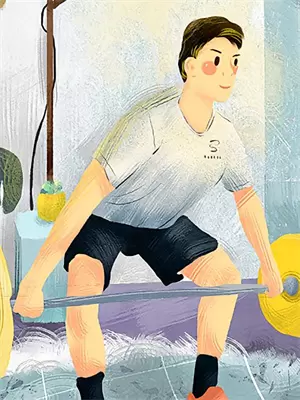
最新评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