鸡叫头遍时,林晚月己经蹲在溪边洗了三把脸。
小穗子抱着比她还高的竹筐,里头装着昨夜腌制的麻辣鱼串、用荷叶包好的野葱饼,还有半罐用野蜂蜜调的甜酱。
“穗子跟紧阿姊,到了镇上别乱跑。”
她把一块旧粗布铺在竹筐上,又插了根野菊花当幌子。
通往镇上的石板路坑洼不平,路过王婶家时,木门“吱呀”一声开了条缝——王婶探出头,鼻尖动了动:“月儿,你这筐里咋这么香?”
“是新琢磨的串儿,王婶要尝尝不?”
林晚月递过去一串腌好的鱼块,竹签是用后山的箭竹削的,削得太急,指尖还留着道浅疤。
王婶咬了口,辣得首吸气:“哎哟!
这味儿跟那县城里的酒楼似的!
月儿,你真该去镇上摆个摊,保准抢了刘屠户家的生意!”
这话提醒了林晚月。
青山镇最热闹的十字街口,向来是卖货的扎堆地。
她带着小穗子挤过挑柴的、卖布的,在一棵歪脖子槐树下放下竹筐——刚铺开粗布,就被戴瓜皮帽的老汉揪住袖子:“哪儿来的丫头?
这地儿早被张婶占了!”
林晚月赔着笑,看见不远处卖菜的张婶正朝这边翻白眼。
她灵机一动,从竹筐里摸出两串鱼丸——昨儿用山鸡肉剁的,混着野藕碎,Q弹得能当乒乓球拍:“大爷,您尝尝我这手打丸子,要是觉得行,我就挪去巷口,不碍着您生意。”
老汉狐疑地咬了口,腮帮子立刻鼓得像青蛙:“哟!
这丸子咋这么有嚼劲?
比我那儿媳妇做的强十倍!
得得得,你就在这儿摆吧,张婶那人啊,就会欺负老实人!”
开张还算顺利。
日上三竿时,竹筐里的串儿卖了大半,小穗子攥着铜板的手都冒了汗。
林晚月正给个农妇包野葱饼,忽然听见街角传来喧哗——“让开让开!
李员外家的马车来了!”
人群潮水般退开,青石板路上扬起灰尘。
林晚月眼疾手快护住竹筐,却见马车帘子掀开条缝,露出半张擦着厚粉的脸——是镇上米铺老板的小妾,正捏着帕子皱眉:“什么味儿?
又辣又腥的,熏死人了!”
赶车的小厮扬起鞭子:“穷鬼摆摊也不看看地方!
溅了我们家夫人的裙子,你们赔得起吗?”
小穗子吓得往林晚月身后躲,手里的铜板“叮”地掉在地上。
林晚月蹲下身捡起钱,忽然想起现代看过的宫廷剧——既然古代讲究尊卑,那她偏要在这权贵面前挣口气。
“这位夫人,您说我这味儿熏人?”
她故意提高嗓门,举着一串麻辣鸡翅晃了晃,“要不您尝尝?
要是觉得不好吃,我立马收摊,再赔您十文钱买香粉。”
周围响起低低的哄笑。
小妾的脸涨得通红,正要发作,马车里忽然传来咳嗽声:“阿翠,别胡闹。”
帘子彻底掀开,露出位穿月白襦裙的少女,怀里抱着只毛茸茸的波斯猫。
她嗅了嗅空气中的辣味,眼睛亮起来:“这是...辣串?
我在长安时吃过一回,没想到这儿也有。”
林晚月立刻递上一串烤得金黄的鱼丸:“姑娘尝尝?
我这丸子里加了野藕,脆生生的。”
少女咬了口,眼睛弯成月牙:“真好吃!
比长安西市的还香!
小翠,给这位姑娘十文钱,再买五串打包带回府。”
小妾瞪了林晚月一眼,极不情愿地扔了枚铜钱过来。
周围的百姓见状,纷纷围上来——连李员外家的千金都夸好吃,这摊子肯定差不了!
日头偏西时,竹筐里只剩最后两串鱼丸。
小穗子攥着油腻腻的钱袋,眼睛亮晶晶的:“阿姊,咱们赚了二十七文!”
“走,先去买糖糕。”
林晚月捏了捏她的小脸,路过米铺时,故意放慢脚步——橱窗里摆着雪白的糯米粉,还有琥珀色的冰糖,这些可都是做甜食的好材料。
“阿姊快看!”
小穗子忽然指着街角的货郎担子,“是拨浪鼓!”
卖货郎是个留着山羊胡的大叔,担子上挂满了胭脂水粉、木梳头绳,还有花花绿绿的拨浪鼓。
林晚月犹豫了一下,摸出两文钱:“穗子,挑个喜欢的。”
小穗子捧着红色拨浪鼓笑得见牙不见眼,鼓面上的小铜铃“叮叮”响。
林晚月看着她蹦蹦跳跳的背影,忽然觉得胸口暖暖的——就算没有男主,没有金手指,只要能让妹妹吃饱穿暖,这穿越,好像也没那么糟。
回家的路上,夕阳把两人影子拉得老长。
小穗子边走边数钱,忽然扯了扯林晚月袖子:“阿姊,明天咱们能做那个...那个炒米粉吗?
隔壁柱子哥说,县城里的米粉软乎乎的,像云彩一样。”
“好,明天咱们就去买米粉。”
林晚月抬头看了看远处的青山,晚风带来草木清香,混着她发间残留的辣椒味。
她摸了摸腰间的《食谱》,忽然想起扉页上不知谁写的小字:“人间烟火气,最抚凡人心。”
大概,这就是她的宿命吧——在这柴米油盐里,熬出属于自己的星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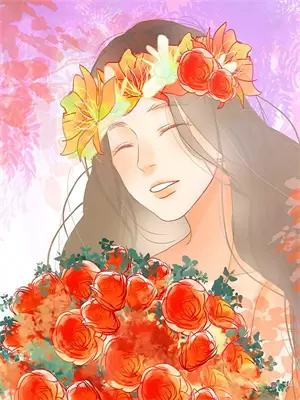
最新评论